摘要:在当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而不断地改革升级的时代下,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引入中国,大大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凡事有利也有弊,滥用公司人格的案件也频出,这些案件通常会有财产和人格混同或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出现,实践中一般都是以此情况作为适用条件。而在司法适用中也出现了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规定不明确,对公共利益保护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和执行程序上的空白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增加对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认定和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将公共利益加入到保护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倒置,执行程序中也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关键词: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司法适用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提出,被作为是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例外。该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支持,“有效遏制了我国出现大量滥用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制度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因为事实情况的复杂和公司的特殊性质,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就要求灵活运用的同时抓住本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正确适用。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诞生于美国的"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各国都通过这项法律来达到控制和限制公司独立人格滥用行为的效果,用来填补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缺陷,是一项体现公平原则的重要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股东不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为了逃避责任、违反诚信原则而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带来损害,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有权透过公司法人人格,直接要求造成损害的控制股东向公司债权人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本质来看,它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补充与维护”,防止因为公司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风险,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有效的将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形象的“圈起来”。
在当今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过于严苛的制度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求规范,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认定其滥用了公司人格。为了保证制度对市场的调控作用,该制度的适用只能在特定的主体和特定的法律关系下,具有“兜底”作用,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讲究效率至上的时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要求更加注重公平:在否认制度被引入前,控制人或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却只用承担自己出资范围内的风险,公司人格独立成为了有些人侵害他人、牟取暴利的工具。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就是在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下,拨乱反正,调整了利益和风险的平衡,保证了市场健康发展。
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一)财产混同和人格混同
当公司被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渗入太深时,公司的财产和股东的财产已经混同,丧失了资本的公司没有办法做出对应资产的经营导致公司人格与公司控制人的人格混同,公司丧失了独立地位,不具备人格独立的资格。因此为了保护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就应该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制裁。如在“韩南保、广东正德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本案的纠纷中存在个人账目与公司账目相混同,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混同,个人人格与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应当对正德置业公司因合同解除所承受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二)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本的多寡决定着公司可以独自承担债务的能力。公司如果做出远超于自身资本的担保或经营活动,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当债权人要求公司赔偿时,公司的资金不足以偿还。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只用承担出资范围内有限的风险,而将大量风险转接给债权人。这种严重侵害债权人的行为例如:“曾小明、合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与曾小明、合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古晓辉与曾小明系夫妻关系,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曾小明与他人共同开设了东莞雷豹公司。东莞雷豹公司因委托加工,对合昌公司负有加工费及货款483158.24元的债务。后东莞雷豹公司因经营不善,2009年6月18日,东莞中院作出裁定,宣告东莞雷豹公司破产。2012年6月22日合昌公司以股东侵犯债权人利益向东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曾小明滥用股东权利,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要求曾小明妻子古晓辉对案涉债务也承担连带责任。东莞中院一审认定曾小明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妻子古晓辉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曾小明不服向广东高院上诉,广东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后曾小明不服向最高院提起再审,但仍被驳回。广东高院认为,“曾小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清楚。曾小明等人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严重失衡,故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曾小明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公司制的特殊性和市场的复杂背景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依然"力有不逮”,虽然司法解释作为补充可以为审判实践提供依据,但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制度适用的实体和程序都存在有很多问题。
(一)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规定处理不明确
《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直接股东,但是却可以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如在“杭州冰垭贸易有限公司与周敏、徐越芬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法院认为,“诚思达公司是借用潘明忠、王丽仙二人名义设立登记,潘明忠、王丽仙并不是公司实际出资人,也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周敏、徐越芬夫妻二人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故周敏、徐越芬符合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特征,应当认定其为诚思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国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规定不多,仍处于起步的阶段,一般的规定只是针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要承担连带责任却没有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导致实际控制人的
责任得不到规制,使其有空可钻。《公司法》在第21条中提到实际控制人,但也只是简单的提出概念,对其责任没有进行规定。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性质并不一样,实际控制人并不会出现在股东名册上,在明面上处于公司外部,但是却对公司有实际控制力。所以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不能只是将其与股东等同,两者是并行的关系。类推适用要求两个主体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是因为公司制度的特殊性导致对待实际控制人无法直接类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的审判此类案件的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根据一般法原理,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人格之行为属事实行为,通常归入侵权行为之列,并以侵权责任涵摄之"。将实际控制人视为侵权人,直接向其提起诉讼。例如:"珠海五金矿产进出口有限公与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珠海广金厨具有限公司、张开炎、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达利金属压制厂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达利公司的股东省五矿公司为达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损害了五金矿产出口公司利益。"
第二种审判方式:审判实际中,法院也会与《民法典》结合审理,因为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在实践中通常都会侵犯公司和债权人利益,在外部的表现上为公司侵害了债权人利益,又在实务中往往由公司独立承担责任,最后实际控制人的侵权行为却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经营讲究“内外有别”,公司理所当然的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但是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配力使公司怠于追偿。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以及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现实中,被侵权人因为债权无法实施而会向法院提出代位撤销之诉,债权人大多只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法院也会围绕诉讼标的来审理,但是对实际控制人的惩罚性目的就无法实现。
以上两种方式的适用仍有缺陷:实际控制人具有间接隐名性导致的间接损害的因果关系能否证成、债权能否成为侵权客体、债权人作为权利人是否满足主体适格要件,不无争议。而且实际控制人对于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是持续长期的,对于侵权的数额不能精细计算,无法满足“债权数额确定”的要求。综上,对于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适用《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篇的关于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规定,虽然为法院审判提供了方法,但是不利于债权人举证、程序上具有局限性、在审判实践中操作难度大等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不适合公司的特殊性质。
(二)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足
因为经济活动需求,“法人制度首先开始于公司,后扩及于非营利的组织。"公司法人注册的放开使公司人格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影响公共利益的组织。作为民商事的法律制度,多数的规范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更注重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却有缺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自由注册,国家为公司法人提供了政治政策的支持,向其倾斜大量社会资源。但是有些公司正是利用国家给予的权利,肆意损害公共利益以追求利益最 大化。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保护公共利益上的缺失导致在审判实践中,被惩罚的往往都是公司或者单位,但知情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却最多只会承担有限责任甚至不负责任。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同时公司人格化也赋予了它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的控制形式”[10](p28)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股东却可以使公司人格制度成为他们的保护膜而逃避责任。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公平
实体法的正确适用离不开程序上的健全制度,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程序规定中,《公司法》对其涉及较少,尤其在举证责任规则方面存在缺失。在实践中,对于关于公司人格否认案中,大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由债权人提出证据证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这样就导致了受侵害方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对于能证明滥用公司人格的证据一般都处于公司内部,不易获得,例如财务报表、账单、财产清单等。而信息披露制度和财务制度规定股东不能轻易取得财务会计账簿和核心材料,对于核心资料复制权的限制都使得公司内部的小股东不宜获得证据,那就更不用提公司外部的债权人。就是因为在程序上的举证规定不明确,导致了债权人、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四)执行程序上的空白
除却在审判程序中证据收集困难的问题,该制度在执行程序上的规定也存在空白。一般在债权人发现股东操控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法院诉讼的过程也给了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时间去转移资产或抽逃资金,导致审判结束后即使要求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责任,也没有资产可以执行。当事人只能再次提出要变更被执行人之诉,使执行更加繁琐复杂。但法律也只是规定侵权股东在其未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所以在执行程序上的缺失仍然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提出的建议
(一)对实际控制人的规定建议
第一点,尽量完善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认定,为了保证公平正义,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从广义的角度看待:法院应该将所有拥有对公司绝对控制力并进行滥用者都认定为实际控制人。不仅要对公司外部的控制人进行认定,也要对公司内部的股东、高管、监事进行调查认定。对于借用他人名义为股东的隐名投资者可以通过“刺破公司双重面纱”来跳过公司人格,实际的惩罚实际控制人,对于拥有控制力的股东、高管等则适用“公司人格混同”的适用条件,不仅追究侵权责任也要其赔偿因未尽到义务而导致的损失。
第二点,把实际控制人也纳入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内。对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规定进行补充,加强监管机制,增加将公司具有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进行登记的规定,这样不仅可以使其现名并承担责任,也大大降低了法院和债权人收集证据的难度,更有利于对公司的管理监督。
(二)对于执行程序的建议
"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置于强制执行程序之中,以强大的执行力起到规范的公示作用,使滥用法人独立人格的股东被追究无限责任”。执行法院对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案件依职权主动进行裁决:如果出现股东在审判期间故意抽逃出资、转移资产的行为,法院可以主动冻结公司资产;如果公司资产被转移导致无法被执行,当事人申请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及执行异议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变更当事人或被执行人,刺破“公司的面纱”直接执行背后隐藏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赋予执行法院这样强大的权力时,在执行过程中,也要有所监督,审慎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否则会物极必反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
结语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秩序地位的不断提高,民商事法律的重要了保障。笔者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规定更加明确、在性日益增长,从《民法典》的颁布中就可见一斑。而作为《公司法》中重要的程序上更加完善、保护范围更加扩大、公平正义原则更加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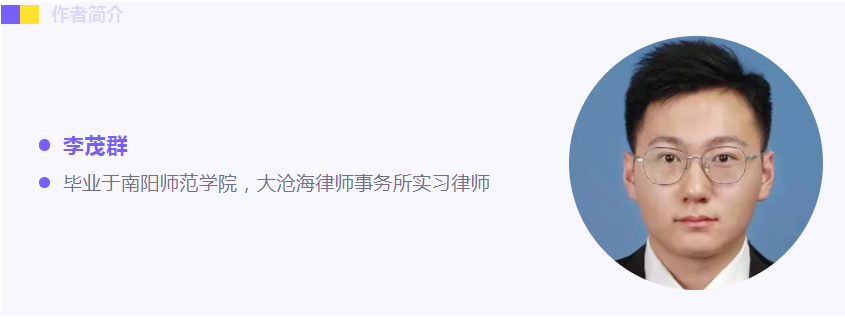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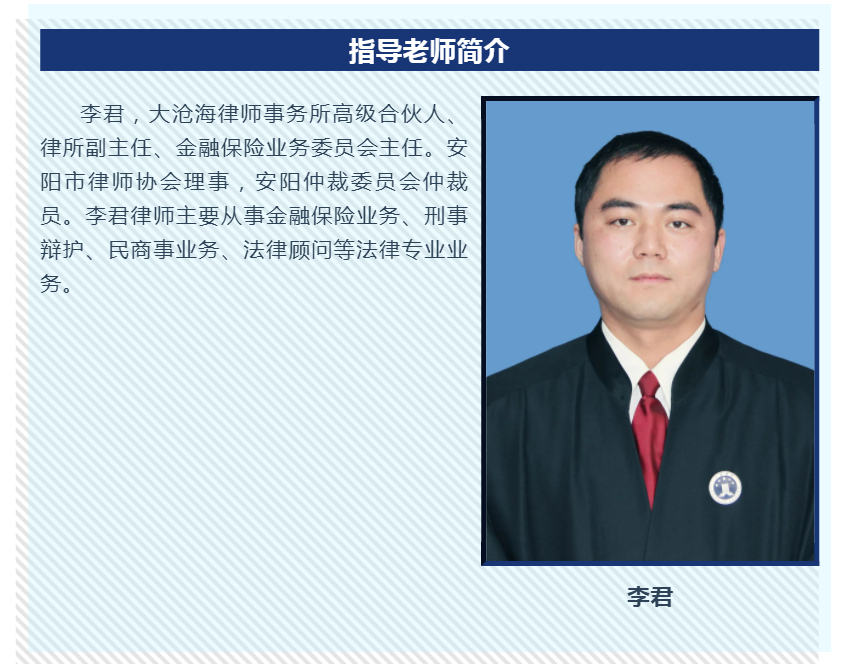
文稿撰写:李茂群
排版制作:贾 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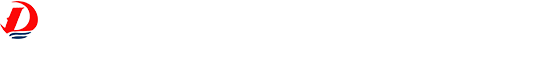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41050202000592号
豫公网安备41050202000592号